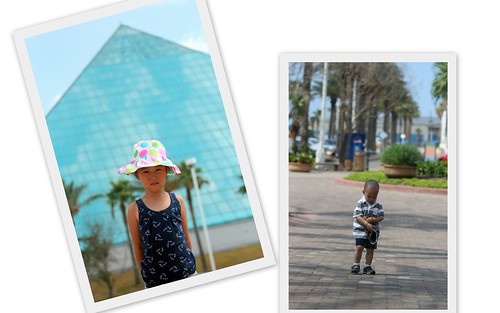去年某天我们举家在costco因为各式样品流连忘返的时候(比如说一个酸奶的摊子,我去要两回,他爸去要两回,我再去要两回,同样的酸奶,买回家就谁都认为味同嚼蜡了,costco的气场实在是不同),两个天鹅一样的小姑娘过来发她们舞蹈学校的传单。胖子酸奶都不吃了,愣愣的看着人家的背影,妈妈,她们真~~~~~~好看啊。
彼时这个人正在热烈跟风她们学校的几个小盆友,要求学芭蕾。她们学校有老师来教,是之前在墨西哥国家剧院演出过的一个美女,一个星期一次,一个月九十块。一个老墨(我真不是种族歧视的人,可是跳芭蕾耶,你赖好也来个前苏联什么吧)组织的野台班子,跟教室里面胡乱的蹦几圈,就敢要我拍这么多钱,我长得真的很冤大头乜?这些话,自然无法跟胖子传达。所以每个星期美女来授课那天我都要胡乱的和胖子搪塞,搪塞来搪塞去,马上就要崩溃了,正要顶着冤大头写支票之际,天鹅姑娘们从天而降。
别的不说,她会计妈妈我chua的一眼就看到了价钱,五十五刀~
如此,胖子的芭蕾生涯就开始了。
跳了两次我大概齐就看出了端倪,这个胖鸭子,你就算给她扔到天鹅窝里,她也跟优雅不达尬。五十五刀,再便宜,它也是美钞。我老人家,这个冤大头,是当定了。
上课的时候,东倒

西歪

抠抠

拽拽

几个小姑娘一起,更是叽叽喳喳,根本就没人专心

一个人要喝水就全都口渴,一个人要去厕所就集体尿急,美国老师又比较写意,完全不在意小盆友动作标准不,到位否,说到底,我老人家还是拍钱讨自家胖鸭子欢心。人家那些天鹅姑娘,多数生下来就是天鹅模样。做妈的啊,就是喜欢有些不符合实际的痴心妄想。
这么拍钱拍着拍着就拍到了年底,学校一纸通知发到家里,五月份有个recital.
我傻乎乎的想,表演就表演吧,反正我已经是冤大头了,干脆一冤到底。签了卖身契,非常之豪迈的拍出五十块场地费。
殊不知,从此,我算是掉到沟里了。大概齐是我脑门子上刻着有字,谁都知道我好骗。
场地费完了是组织费,组织费完了是服装费,服装费完了是摄影费,摄影费完了,居然号召我们大家给自己闺女献~花~,整整一圈忙完,我拍钱拍得两眼发花之际,又一纸通知下来,好家伙的,这一场从头到尾都是我们拍钱办的演出,我们这些大善人~还得~买!门!票!
NND,我这么没骨气的人又放不出“老娘不干了”这种狠话,打碎了牙活血吞,三孙子似的去买门票。
卖票的说啥,卖~完~~~~~~~~了。
见过拍出去几百块连响儿都听不到的len么?我老人家险些就在镜子里面见到了。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票,终于买到了,价钱都没问就高叫,我要我要我要~~~~还美的什么似的,你说我这个人,不是二百五,是什么?!
买到票的这天,一直旁观的领导终于长出一口气,这下总算消停了吧?
自然没有。
演出前三周,照相。我这个人命苦啊,小盆友学个跳舞,也要赶上个韩国同学。相照得倒是很好,一不小心还上了海报

问题是胖子看上了韩国同学那晶莹剔透无可挑剔的妆容。
这之后的几周,就看见她朴实无华还轻度色盲的妈妈,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网路上面乱转,
逮住谁问谁,怎么化妆啊怎么化妆。
众多美女合议之后,一杆子,我就被支到了一个叫做sephora的神圣所在。
但见我这个土包子,扛着一摞打印资料就杀进了sephora,大约是我research超级充分的场面比较吓人,也大约是我tshirt破裤子flipflop外带浮肿眼袋黑黄脸色的整体造型更加吓人,在店里整整四十分钟啊,传说中超级热情的sephora sales硬是没有一个人理我。结帐的时候,我跟着计价器默念,粉底,四十二刀,散粉,四十二刀,腮红,三十七刀,唇彩,二十四刀...做一个二十四孝老妈,priceless。
晚上领导看着账单长叹,两百多块!!!!!你行不行啊你。
我想想背后无数美女老师的强大的队伍,非常虚弱的答,大概。。。。。。不行。。。。。。
行也好,不行也好,recital这个周末,它总是要来的。
星期六一大早就要彩排。提前一个小时,我把买来的瓶瓶罐罐们在桌子上摊开,就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化妆运动。一边画,还一边把
shuyi推荐的
youtube video在旁边滚动播放。化了擦擦了化,一直忙到要迟到,作品总算是出炉了:

完全不体谅她妈妈我苦心的人啊,在车上在彩排现场一直到回到家,念了整整一天,妈妈我一点也不colorful!妈妈你化的不好看!
什么叫冤大头,什么叫二百五,就是连五岁小盆友都可以随意指使的人。
于是,第二天正式演出,我干脆豁出去了,也不管什么韩流不韩流,也不管什么小盆友自然美不自然美,哪个怯哪个艳就哪个往小盆友脸上招呼,招呼完了,是这么一般的情景

我跟在她后面都想挂一个“她的妆不是我画得”的牌子。
可是小盆友们显然都很欣赏她这个妆容,一副看不够的样子

每个看到她的十岁以下的小姑娘都会由衷的感叹,WOW~YOU ARE SOOOOOOOO PINK!
有耐心看到这里的同志,大概认为,我的冤大头生涯,就要结束了,自然,还是没有!
停车,四块,要不要停?!要!(我不会平行趴车)
节目单,三块,要不要买?!要!
白水忘了带,三块,要不要买?!当然要!还要买两瓶!好叫她跟小盆友分。
献花,五块,要不要?!我都纠结了大半年打算守住这最后一道防线的,可是,看看进出的家长无不一人一支花,好,献!
酱紫,揣着节目单,白水,鲜花,大包小包扛着化妆品外加摄像机,照相机还有一个重得要命的镜头,的老妈子
看着门口老大一个NO PHOTOGRAPHY的告示发呆
旁边一个熟人过来捅我,哎,你不是group mom嘛,去后门集合啦~~~~~~
做这个group mom呢,也是机缘巧合
这个group,三个小盆友,一个韩国妈妈,不会说英文,一个美国妈妈,家里另外还有三个宝宝,场场缺席,所以我不知道在哪个猴年哪个马月签过名字,从此也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。
又赶上大概所有的妈妈们都身经百战集体门清,所以谁也不解释谁也不嘱咐,到点儿就指望你闪亮登场。
我傻乎乎的带着胖子跑到化妆间的时候,看到满屋子的娃娃们穿插着个别盛装打扮的妈咪,每个都气定神闲的管理着十多个孩子,这个补补妆那个梳梳头,个个打扮得妥妥贴贴。
我想,虽然我灰头土脸穿着snoopy tshirt,但是!我就管三个娃娃嘛,假装一个神态自若应该还是不难。于是我打发娃娃们去画画,自己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倒气。
胖子的节目是第二个,所以她们去上台的时候,时间还很早,我再次左一包右一包把我那些完全没有用的装备扛好,准备向高价艰苦买来的超好座位进发。
还没有走到门口,一个花枝招展的妈妈过来,哎,你一会儿还要回来呃,你group里面的zoe,下一场,要跳我们这个tap哦~
酱紫,我扛着一堆包,说了一万个道歉,摸黑挤到我第三排正中的座位做好,卸下包袱,违反规定的偷偷照了相,




又扛着一堆包,说了一万个道歉,抹黑挤出我的超好座位,跑回后台。
后台口花枝招展的妈妈又来了,哎,你怎么才来啊,快去快去叫zoe啊~
于是我托着包袱,几个台阶一跳跳到化妆间,zoe zoe!啊呀要死了你的衣服怎么还没有换!
zoe很有礼貌的放下蜡笔,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!
胖子在旁边很有礼貌的放下蜡笔帮我翻译,she said she's gonna die since you haven't changed!
刚刚扒光了换好,zoe又很有礼貌的提醒我,i need to change me tights too!
。。。
重新来过。
终于换好了,我扛起zoe就跑,也是个五十来胖的胖娃娃啊,跳下三楼,刚好tap dance要入场
花枝招展的妈妈又是一声尖叫,her hairpiece~~~~~~~~~~~~~~~~~~~~~
酱紫就算完了么?还是,没有!
zoe这个小盆友,她,还要再跳,JAZZ!
整整一场演出,就看我一个人上窜下跳了。我上下求索高价买来的票啊,也就是心不在焉的看了一眼胖子不三不四的所谓芭蕾。
人类历史上,跟我这等冤情类似的,不多了吧?!
更加冤的是,曲终人散,小盆友哭了,妈妈~~~~~~~~~我不要演出结束~~~~~~我明年还要演~我要像ZOE一样,跳三个舞~~~~~~~~~~
于是,胖子的芭蕾生涯,以及 她妈妈我的冤大头生涯 还要继续。